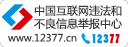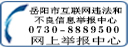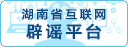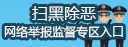□徐 輝
我想,我注定是會(huì)和這座古塔相遇的。
因工作緣故,今年我有機(jī)會(huì)一次又一次走進(jìn)長江之濱的臨湘塔生態(tài)文化園,只見白馬磯上、儒磯山頭,灰白相間的臨湘塔煥然一新,與碧水江天相互映襯。
江邊有釣者,與之閑聊,我得知臨湘塔的前世今生。臨湘塔建于清光緒七年(1881年),現(xiàn)保存基本完好。1881年,臨湘人劉璈做浙江臺(tái)州知府時(shí),為了助力家鄉(xiāng)文化教育發(fā)展,捐資在儒磯山建八面七級(jí)、高33米的寶塔,是為臨湘塔。“側(cè)疊萬古石,橫為白馬磯。”唐代詩人李白曾到此訪友,寫下名篇《至鴨欄驛上白馬磯贈(zèng)裴侍御》。塔銘《臨湘塔記》,則由光緒乙丑科舉進(jìn)士吳獬撰寫,鑲嵌于首層外壁上。吳獬《臨湘塔記》一文含蓄詼諧,充滿著社會(huì)哲理和睿智,其對(duì)科舉文化的深刻理解,超乎常人,也超越其所處的歷史時(shí)代,具有較高的文史價(jià)值和思想價(jià)值,一時(shí)讓臨湘塔美名遠(yuǎn)揚(yáng)。
然而,隨著歲月變遷,塔遭風(fēng)侵雨蝕,周邊私搭亂建,污染越來越重,讓它失去昔日風(fēng)采。近年來,臨湘市啟動(dòng)最美長江岸線臨湘塔段項(xiàng)目建設(shè),按照自然美、生態(tài)美、人文美理念,以臨湘塔為軸心,整合資金對(duì)周邊的自然山體、黑臭水體、灘涂、草地進(jìn)行生態(tài)修復(fù),逐步建成臨湘塔生態(tài)文化園、文化展示館、可拆卸式游客服務(wù)中心驛站等公共服務(wù)設(shè)施,形成了“山、水、塔、洲、渡”于一體的獨(dú)特風(fēng)光。古樸的臨湘塔,串起一個(gè)個(gè)生態(tài)景點(diǎn),構(gòu)筑起一條長長的長江生態(tài)文化走廊,成為最美長江岸線上的一顆耀眼的“新星”,重新煥發(fā)出勃勃生機(jī),重現(xiàn)了昔日的美麗風(fēng)彩。
走近臨湘塔,我唯有仰望。眼前的古塔為磚石結(jié)構(gòu),七級(jí)八方塔座為八方形三級(jí)花崗巖塔基座,塔基座以上的每層塔身,均下設(shè)束腰磚座,上出疊澀磚檐,八角檐皆出麻石脊翹,石翹頸系鐵質(zhì)風(fēng)鐸。塔身每層及下檐外粉白灰,下檐冰盤曾施彩繪。古塔的確夠古老了,明顯有些傾斜了,歲月的風(fēng)雨已將塔身洗得泛黃,它的模樣讓我想起了岳陽那座臨近洞庭湖,同樣蒼老的慈氏塔。仰視古塔,感覺微雨中的古塔更顯出幾分唐宋遺韻的冷清和厚重。
佇立江邊,聆聽江濤拍岸,若有江鳥低鳴著從眼前掠過,只留下詩意的弧線。臨湘塔與江水相伴千年,古塔早已化琴者,獨(dú)坐幽臺(tái)上,以江水橫琴,彈琴復(fù)長嘯,日夜彈奏千古清音和人間絕唱。高塔流水,一人一琴,一靜一動(dòng),古塔與江水想必早已是人世間最美妙最逍遙的逸士妙人了吧!
在與古塔的默默對(duì)視間,我猛然頓悟,觀塔如觀人,塔是人按照自己的思想建造的,建塔為供神,而神是人性的神性化,人們頂禮膜拜的表面上是一座塔,其實(shí)是神性的人,是心中另一個(gè)真實(shí)且完美的自我。
走近臨湘塔,觀照自己的內(nèi)心。臨湘塔讓我頓悟,讓我感到快樂而滿足。這也是我在走近臨湘塔前萬萬沒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