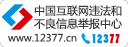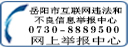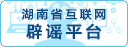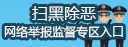□劉衍清 吳健體
照相技術(shù)于1844年由法國人于勒·埃及爾傳入中國澳門、廣州,從此逐漸由南到北,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擴(kuò)展。岳陽的照相業(yè)的歷史可追溯到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距今已有133年。筆者近日查閱相關(guān)資料,先后走訪了幾位90多歲的照相業(yè)老前輩,并根據(jù)作者個(gè)人親歷回顧岳陽照相館用光與影凝結(jié)的故事。
羊叉街開啟光與影的序幕
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岳陽人汪繼真在縣城羊叉街開設(shè)了照相館,一直未命名。因當(dāng)時(shí)科學(xué)知識(shí)尚未普及,有人傳言照相底片是用紅色藥水沖洗的,系攝入了人體的血液所致,群眾信以為真,誤以為照相會(huì)吸血、照了折壽。因此照相的顧客日漸稀少而歇業(yè)。
光緒三十年(1904年),長江水師兵營炮艦駐扎岳陽,其水師首領(lǐng)之子余松齋(湖北人)酷愛攝影,遂由其父送到武昌黃鶴樓顯真樓照相館當(dāng)學(xué)徒。宣統(tǒng)末年(1911年),余松齋藝成回岳,與汪繼真族弟汪繼成(又名汪劍溪)合伙在與羊叉街交界的油榨嶺開設(shè)了“玉壺冰”照相館。1913年,棚廠街小學(xué)教員汪幼孚三子汪潔吾在“玉壺冰”照相館學(xué)習(xí)三年后,與二兄汪慎吾在縣門口開辦了“容華”照相館。汪家兄弟經(jīng)營有方,照相業(yè)務(wù)越做越活,遂于1930年分設(shè)照相館,由汪慎吾花光洋二千三百元置羊叉街何某房屋一棟開“容華”照相館,汪潔吾則仍在老縣門口開設(shè)“榮華”照相館。
除余松齋的“玉壺冰”、汪慎吾和汪潔吾兄弟的“容華”“榮華”以外,湖北人吳新庭、吳金元兄弟和孫鳳池也先后來岳陽開設(shè)了照相館。其中1927年由湖北鄂城進(jìn)入岳陽的吳新庭、吳金元兄弟與負(fù)責(zé)管理岳陽樓的道長簽約,進(jìn)入岳陽樓兩側(cè)的“三醉亭”與“仙梅亭”,分別開設(shè)了“天然”和“金元”照相館。
由于岳陽城關(guān)地處南北交通要道,外來商旅眾多,而當(dāng)時(shí)下火車后,岳陽城內(nèi)只有經(jīng)先鋒路、塔前街、羊叉街、天岳山、南正街過吊橋至岳陽樓一條“直腸子”街道。因此,隨后一些照相行業(yè)從業(yè)人員開辦的照相館大都分布在這條如今統(tǒng)稱洞庭南路歷史文化街區(qū)的老城區(qū)域。除“玉壺冰”“容華”“榮華”以外,還有天岳山的“楚華樓”、油榨嶺的“留真”、吊橋的“宛在軒”及后來羊叉街的“銀星”等照相館。
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日機(jī)多次轟炸岳陽城,迫使居民疏散,商鋪關(guān)門。1938年日寇侵占岳陽前夕,“容華”“榮華”“玉壺冰”分別遷往岳陽縣渭洞、華容縣注滋口。其他遷往沅江南大膳等地另謀生計(jì)。只有在“天然”“金元”吳氏兄弟店里擔(dān)任照相技師的叔叔,不放心兩位侄子的家業(yè),執(zhí)意留下守店,結(jié)果因抵觸日寇被槍殺。日寇占領(lǐng)岳陽8年,只有“大冢”等兩家由日本人所開的照相館(分別開在油榨嶺和茶巷子)靠拍攝所謂“良民證”上的照片盤剝難民。
抗戰(zhàn)勝利后,岳陽照相館業(yè)主陸續(xù)復(fù)業(yè)。其中湖北人孫鳳池在岳陽樓下開設(shè)了“銀光”照相館,其子孫建民在羊叉街開設(shè)了“銀星”照相館。另有趙考?jí)墼诓柘镒娱_設(shè)了“遠(yuǎn)東”和“唯一樓”兩家照相館。城區(qū)內(nèi)照相業(yè)全部經(jīng)營日光黑白照相,內(nèi)置玻璃攝影棚,采用藍(lán)布、白布活動(dòng)調(diào)光,照相機(jī)一般為德國產(chǎn)蔡斯、“蔡納”鏡頭,攝影使用德制“埃克法”和美制“柯達(dá)”膠卷,也有使用“柯達(dá)”顏料色譜,在黑白照片上手工加繪彩色。也有攝影師走出店門,串街入巷,上門拍照,收費(fèi)一般略高于店堂,2寸照銀圓6角,4寸照則價(jià)格加倍。
新中國成立后,社會(huì)穩(wěn)定,岳陽城里的私人照相館發(fā)展到23家,設(shè)備仍較簡陋,借用日光在玻璃棚內(nèi)照相,用活動(dòng)木制框玻璃架印相。底片與相紙夾在架內(nèi),計(jì)時(shí)以口報(bào)數(shù)字為準(zhǔn),用日光曝光,用紅紙貼在煤油燈上遮住光線洗相。1956年公私合營,合為7家公私合營照相館。隨后又精簡到“天然”“湖山”“容華”三大照相館。隨著城區(qū)普及供電照明,照相工藝有所改善,布景式樣增多,攝影效果增強(qiáng)。20世紀(jì)60年代至70年代,照相工藝有了改進(jìn),開始用自動(dòng)快門電光照相和紅光電燈洗相,并采用了電子定時(shí)印相機(jī)印相,操作比較靈敏方便且質(zhì)量可靠。1970年開始,位于南正街的“旭日”照相館開始經(jīng)營照相器材。但在那個(gè)特殊時(shí)期,講美即是“封資修”,店里規(guī)定只能拍正面照,只能著青、藍(lán)和綠色服飾照,布景、姿勢、發(fā)型等均有限制。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ì)后,撥亂反正,照相行業(yè)迅速發(fā)展,“光和影”的照相技術(shù)和原來可望而不可及的照相器材也逐步走入尋常百姓家。
照相人不為人知的故事
照相機(jī)普及之前,岳陽城區(qū)從事專業(yè)照相的人并不多,從清末到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照相館從業(yè)人員僅發(fā)展到62人。即使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1956年公私合營,照相館在冊(cè)員工也還只有70人。在這人數(shù)極少的隊(duì)伍中,人們很少知道他們的故事。在搜集洞庭南路歷史文化街區(qū)百年故事的過程中,我們從中擷取了幾朵浪花:
1945年日寇投降后,逃難回來的吳新庭在靠岳陽樓三醉亭恢復(fù)了“天然”照相館的營業(yè)。吳金元在仙梅亭的“金元”照相館也重新開業(yè)。1948年,原國民黨國防部長白崇禧一行軍政要員,來岳陽樓游覽后拍照合影。當(dāng)年“天然”照相館的吳新庭支起老式相機(jī)座架,看著荷槍實(shí)彈和全副武裝的軍人,心里異常緊張,慌忙中將6寸膠片暗盒當(dāng)作8寸暗盒使用。
當(dāng)照片洗出來后,才發(fā)現(xiàn)底片小了,合影人群中兩邊站立的人物有些未照進(jìn)去。當(dāng)時(shí)吳新庭一家人嚇得差點(diǎn)跑路。隨后勤務(wù)兵拿照片,看見中間坐著的白崇禧等要員在其中,便匆匆拿著照片走了,幸免了一場災(zāi)禍。
而“銀光”照相館的孫鳳池卻沒有這樣幸運(yùn)。他在抗戰(zhàn)勝利前夕,為了養(yǎng)家糊口,背著一只沉甸甸的箱子,裝著簡易的照相洗相設(shè)備來到岳陽城里,慢慢積累開了一家“銀光”照相館。“文革”中,他不經(jīng)意間說漏了一句話,讓人知道他在武漢黃鶴樓照相館做學(xué)徒時(shí)曾給前來游覽的蔣介石拍過一張照片。被人揭發(fā)后當(dāng)即被審查關(guān)押,送到農(nóng)場監(jiān)督勞動(dòng)半年之久。
從19世紀(jì)末到20世紀(jì)30年代中期,岳陽照相館從業(yè)人員主要是汪氏家族,有汪繼真、汪繼成、汪潔吾、汪慎吾等。而從20世紀(jì)30年代到60年代,岳陽城區(qū)照相館吳、孫兩姓幾乎占了半壁河山。當(dāng)年照相行業(yè)公私合營時(shí)入冊(cè)的只有70人,而吳家和孫家子孫后代從業(yè)者眾多,如吳新庭、吳金元、吳繼昌、孫鳳池、孫建民、孫建麗等,稱得上是照相世家。那個(gè)年代,照相業(yè)作為一門技術(shù)活、經(jīng)驗(yàn)活,拍照講究用光和角度,沖洗須經(jīng)多道復(fù)雜工序。入行照相技術(shù)工種需要3年學(xué)徒期,照相業(yè)的攝影師、暗室?guī)煛⒄迬煟ㄐ薨妫⒅ú噬煹榷际羌夹g(shù)含量較高的工作,因此過去的照相從業(yè)人員多系家傳。后來岳陽城區(qū)照相業(yè)納入國營,在商業(yè)系統(tǒng)屬于特種行業(yè)。
“天然”照相館吳繼昌老師傅,練就一手修底片絕活,全憑一雙巧手,用簡單的鉛筆、毛筆、修復(fù)刀勾勒出底片完整輪廓。尤其是顧客照相時(shí)眼睛眨了,他能在底片上修復(fù)好,避免顧客重新照相。
在老一輩照相館師傅中出現(xiàn)了一大批照相高手,他們?yōu)轭櫩团臄z的各種人物照片,有的被作為樣板展在櫥窗里,成為當(dāng)時(shí)除電影、戲劇之外岳陽城頭唯一的“街頭文化”,也成就了不少愛情佳話。如當(dāng)時(shí)一位“姊妹理發(fā)店”的女理發(fā)師,因面容姣好被拍成模特展示在照相館的櫥窗內(nèi),引來不少追求者,不久這位“理發(fā)西施”就被巴陵戲劇團(tuán)的一位名角追求。還有從羊叉街“容華”照相館調(diào)到“岳陽樓”照相館的戴陽生為當(dāng)年下放君山茶場的女知青謝元元拍了一張英姿颯爽的女民兵形象展在櫥窗內(nèi)。60多年過去了,人們?nèi)詫?duì)這張英姿颯爽的照片記憶猶新。
光與影凝結(jié)成的時(shí)光印記
從20世紀(jì)80年代起,隨著時(shí)代的發(fā)展,岳陽國有照相行業(yè)逐漸衰退。原“旭日”照相館老員工文光楚成為行業(yè)第一個(gè)敢吃螃蟹的開拓者,他獨(dú)自跳出國營行業(yè),干起個(gè)體照相。之后開設(shè)“青春”和“巴黎”照相館,在岳陽城區(qū)名噪一時(shí)。接著,曾當(dāng)過攝影公司一把手的陳漢湘也在南湖大道開辦了一家“迎賓”攝影社,憑著他高超的攝影技術(shù)贏得社會(huì)各界的高度贊揚(yáng),連市里每次重大的領(lǐng)導(dǎo)接待活動(dòng)都是安排他擔(dān)負(fù)集體合影任務(wù)。
隨著市場全面放開、科技進(jìn)步和數(shù)碼攝像技術(shù)的飛速發(fā)展,照相行業(yè)的門檻不斷降低,便利的小型數(shù)碼照相館出現(xiàn)在街頭巷尾,尤其是手機(jī)照相功能的普及,使得傳統(tǒng)的國營照相館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逐漸被邊緣化、市場化。2010年,全市商業(yè)系統(tǒng)原有企業(yè)與人員實(shí)行全體改制,目前僅南正街“旭日”照相館還保留這塊招牌,由全市照相行業(yè)第一個(gè)加入黨組織的女共產(chǎn)黨員、國有攝影公司最后一任黨支部書記孫建麗延續(xù)岳陽照相業(yè)百年來的經(jīng)營業(yè)務(wù)。孫建麗16歲就繼承老父親孫鳳池和兄長的事業(yè)加入照相館工作,從事過照相、洗相、放相、修相、修底片、彩擴(kuò)等工作,是個(gè)傳統(tǒng)照相館的“全褂子”。她在國有攝影公司所有員工得到安置后成為“旭日”照相館的最后一名值守者。今年68歲的她不管刮風(fēng)下雨,每天一早堅(jiān)持打開店門迎接顧客,此舉既照顧了幾代人凝成的照相情結(jié),也為洞庭南路老街留下了百年歷史文化印證,樓上還保存著幾代人用過的照相器材。
過去百年,汪繼真、汪慎吾、吳新庭、吳金元、孫鳳池、孫建民、方繼建、楊建君、嚴(yán)望開等照相行業(yè)的前輩們用光和影為千千萬萬的顧客和他們的家庭留下了難忘的記憶,那一張張用雙手拍攝洗印的照片在人們心中凝結(jié)成永不褪色的時(shí)光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