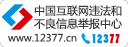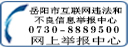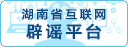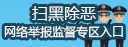□彭仁滿
公元1046年,慶歷新政的余燼未冷,范仲淹在河南鄧州收到一卷《洞庭秋月圖》。展開畫軸,磊石山十二峰如青螺倒懸洞庭,山腳汨羅淵水波如鏡。
此時,滕子京正將磊石山上唐代岳陽樓的殘存梁柱、雕花青石秘密遷筑巴陵新城。這座盛唐文人筆下的楚文化精魂鑄就的天下名樓,自此風(fēng)流于岳陽城頭千年。
當(dāng)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揮毫“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時,月光穿破時空的帷幕,悄然映照著湖畔那座被遺忘的磊石孤山。今人只道岳陽樓在湖畔巍峨,卻不知這座名樓的“岳陽”原點,早已在磊石山下生根千年。
1
磊石山并非尋常丘陵。《元和郡縣圖志》:“岳州本巴陵縣,古羅子國地,在磊石山西南。”《元豐九域志》:“岳州巴陵縣,舊治磊石山南,后徙今治。”兩部官修地志的筆鋒如鑿,將岳陽城原始坐標(biāo)刻在磊石山麓——三國東吳所筑巴陵城,正是岳陽城最初的血脈胚胎。
“岳陽”之謎的鑰匙,藏在“天岳”二字間。洞庭湖口的磊石山海拔近百米,控扼湘資沅澧汨與大江六水歸流之要沖,恰是《說文解字》所載“主四方之水”的“大岳”化身。《荊楚歲時記》注文:“巴陵天岳,乃洞庭東陵之鎮(zhèn)。”
磊石山古名“洞庭山”,亦號“東陵”,唐代《岳陽風(fēng)土記》殘篇“磊石山,岳陽之望,俗呼天岳”。敦煌遺書《葉凈能詩》記載唐玄宗問道士:“洞庭天岳在何所?”答曰:“巴陵磊石山是也。”
張說《岳陽樓石銘序》明證:“開元三年,新作斯樓于洞庭之涘……以妥湘靈”。明人范致明在《岳陽風(fēng)土記》中踏訪過廢墟:“磊石山軒轅臺側(cè)有古樓基,傳為張說故址……石柱尚存。”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岳州城樓,望洞庭東陵如案。”
李白寫“樓觀岳陽盡,川迥洞庭開”,杜甫寫“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岳陽風(fēng)土記》記載的奇觀“磊石山望洞庭,日月若出沒其中”——正是真實畫卷。
幾百年后,滕子京將殘樓北遷今址,南宋王象之在《輿地紀(jì)勝》中留下證言:“岳陽樓初在磊石山,慶歷間滕子京徙筑巴陵城西。”
2
范仲淹“銜遠(yuǎn)山”的秘密在此昭然。磊石山如鷹,鷹喙巖正對百里外的南岳;“吞長江”的玄機(jī)是江水自北奔涌至十二洞天,與鏡湖激蕩旋入地下溶洞。
捧起《楚辭》,驚覺范公筆下處處是其幽微倒影。“朝暉夕陰”實為時空儀式,投射為“登昆侖兮食玉英”的楚地玉祭,“靜影沉璧”就悄然復(fù)活獨清獨醒的鏡像倒影。
“淫雨霏霏”時,《涉江》的苦雨穿越時空而來,“霰雪紛其無垠兮,云霏霏而承宇”。“濁浪排空”之際,《哀郢》的悲鳴在波濤中回響:“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待到“薄暮冥冥,虎嘯猿啼”,《招魂》中險惡之境重現(xiàn)“雄虺九首,往來儵忽”。
春和景明時,“岸芷汀蘭”在“沅有茝兮澧有蘭”的暗香中浮動;“沙鷗翔集”藏著《湘君》“鳥次兮屋上”的輕盈;“浩浩湯湯”分明是《懷沙》“浩浩沅湘,分流汨兮”的回響。
3
范仲淹將屈原沉江的磊石山設(shè)定為隱形的中心坐標(biāo),使“北通巫峽,南極瀟湘”暗指通向楚辭圣地的水路。“遷客騷人,多會于此”的“此”,實乃屈原魂歸的磊石淵藪——賈誼憑吊、李白醉吟、杜甫涕泣的歷史磁場在此凝結(jié)。
屈子以“寧赴湘流”成就殉道絕唱,范仲淹卻“感極而悲”進(jìn)行反撥。當(dāng)洞庭化作“錦鱗游泳”的生機(jī)世界,《漁父》中“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的逍遙,終于升華為“寵辱偕忘”的達(dá)觀之境。
當(dāng)屈子《離騷》“哀民生之多艱”的孤憤,遇見《思美人》“又無行媒兮”的郁結(jié),范仲淹以“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yuǎn)則憂其君”將其淬煉為士大夫的永恒信條。
面對《懷沙》“知死不可讓,愿勿愛兮”的終極抉擇,他給出石破天驚的答案:“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堅定濟(jì)世永生的責(zé)任擔(dān)當(dāng)。
當(dāng)屈原《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在范仲淹“噫!微斯人,吾誰與歸?”的浩嘆中發(fā)出共鳴聲,這座由《楚辭》棟梁架起來的岳陽樓,就不再是澄碧于汨羅鏡湖的洞庭秋月,而是高懸時空中一輪不墜的太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