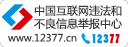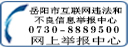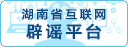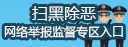1939年9月18日,日寇10萬余人進攻長沙會戰的第一道防線——新墻河。在當地政府號召動員下,在中共湘鄂贛及岳陽地下黨推動下,新墻河成為湘北軍民用血肉筑成的堅強防線。國軍第52軍2師8團1營機槍連上等兵曹錫一晝夜在新墻河王街坊戰場智勇擊殺五百日寇。我市作家徐載滿根據這一真實事跡,用時兩年多,采寫創作了長篇歷史紀實小說《烽火兵王》。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值此之際,我們推出湖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陳善君及作家任福階、舒常敏針對該書的一組評論文章,向英勇抗戰的中國人民致敬!
縱橫捭闔還原“湘北”大捷
精雕細刻塑造“兵王”形象
陳善君
作為岳陽新墻河的子弟,作家徐載滿滿懷感情與責任,歷時兩年多近1000個日夜,輾轉奔波于湖南岳陽、常德、衡陽,陜西漢中及湖北武漢等地,收集整理消化抗日戰爭時期與湘北會戰相關史料,數易其稿,創作出版長篇歷史紀實小說《烽火兵王》(團結出版社近期出版)。
小說以陜西漢中籍國民革命軍第52軍機槍連上等兵曹錫為原型,圍繞第一次長沙會戰湘北大捷真實歷史事件展開,生動講述了新墻河兩岸抗日軍民浴血奮戰的英雄事跡,成功塑造了“烽火兵王”的英雄形象,追敘了英雄的成長經歷,為抗日英雄立傳、為岳陽人民的母親河之一——新墻河銘史。
一、以“大歷史觀”燭照,全面深度還原“湘北大捷”的真實與慘烈
小說28萬字,配上當時敵我兩方作戰的地圖以及有關圖片,通過對“兵王”曹錫及其戰友甘永小、焦曉天、謝小羊、楚武生,以及以甘松青父子、許成章兄弟、舒再興、亢學梅等為代表的一批國共抗日軍民濃墨重彩地描寫和敘述,用文字深情講述了戰役的全過程,藝術再現了湘北會戰的悲壯慘烈。新墻河無聲無息日夜流淌,卻永遠是抗日戰爭的一面鏡子,映照、見證和記載了湘北兒女與抗日戰士曾經在此并肩戰斗的可歌可泣的光榮史詩。小說的高潮和最動人的地方,在于曹錫孤軍殺敵和最后舍身成仁的逼真描繪,而最精彩和最成功的地方卻體現在小說具有的“大歷史觀”。
小說把新墻河大捷放在中日22次大會戰的整體視域下來觀照,放進長沙第一次會戰的整體部署中來反映,這就拉伸了小說歷史敘述的長度;小說不僅描繪國民革命軍英勇的正面戰場抗擊,也反映了中共湘鄂贛及岳陽地下黨發揮的重要作用,這就延展了小說歷史敘述的寬度;小說把中日戰爭包括這場戰斗的矛頭,對準在日本軍國主義的貪婪殘暴與中國人民愛好和平反抗壓迫的較量上,這就具備了小說歷史敘述的深度;小說不僅從中國人民、中國媒體的視角來寫戰爭,還從日本各方、外國各界的視角來寫戰爭,這就拓展了小說歷史敘述的維度。因為作者如是的“大歷史觀”,這場戰爭的真實度和慘烈度在書中能得以更加客觀充分的呈現。
二、以“大文學觀”契入,有機統一縫合“紀實小說”的事實與虛構
《烽火兵王》的紀實性明顯強于文學性。因其歷史事實本身就具備傳奇性、故事性,吸引力和感染力,作者只需“如實招來”,就足以“驚天地、泣鬼神”。日寇的細菌戰和嗜殺成性,往往讓人不寒而栗。于此根本就無須“添油加醋”,就能感受到人間慘劇的“恐懼與顫栗”。作者寫得越“真”,讀者感到越“怕”,產生的力量越“強”,所以《烽火兵王》的“實”有“實”的理由。然而畢竟是小說創作,“兵王”的一生,更多的是“留白”;“戰爭”的勝負結果是已知的,而其過程是“已逝”的。只有虛構,才能完成小說的“起承轉合”,才能讓人物“站立”起來。

曹錫孤軍戰王街坊
小說中的人物在現實中是有原型的,從主人公曹錫開始,曹錫是確有其人其名的,他在“湘北會戰”中,當戰友們都倒下后,仍頑強地堅守陣地,殺敵約500個。他的事跡還登過《大剛報》《大公報》,書中說到被國民政府獎勵了30塊銀元,也是真有其事,軍中號稱“兵王”也不假。如今新墻河抗戰史實陳列館里,還有他的事跡介紹。作者在小說的扉頁列了《人物小傳》,統計了涉及的抗戰軍民,計有33人。除曹錫外,田漢、甘松青等中共地下黨和文藝工作者,還有甘永小、焦曉天、謝小羊、王明光等屬于國民革命軍第五十二軍的戰士,以及時任岳陽縣縣長黎光文等等大都是真有其人其事的。甚至包括幾個漢奸,都是確有其人,曹錫妻子韋素英、同學亢學梅虛構其人其事的可能性和成分比較大。究其分量來看,《烽火兵王》的虛構占到一半,然論其重要性,則不足十分之一矣。一虛一實、一補一貼,“兵王”就活在人們的眼前和腦海了。
三、以“大創作觀”統攝,內外兼顧形成“超文本”的文學與文化
單論文學性,《烽火兵王》并不見長,倘論“文本”性,其綜合價值則高。《烽火兵王》熔史記、傳記、游記、雜記于一爐。其為新墻河“大捷”存史、為“兵王”立傳,也為湖南岳陽和陜西漢中推薦旅游資源。小說中通過追敘曹錫成長歷程,通過他上山砍柴、走親訪友、求學遠足、任職立業、婚娶成家的人生經歷,巧妙地將“石門棧道”、諸葛亮在漢中留下的武侯祠、著名的書法碑帖原型地等著名的風景和文史勝景寫進書中。之于岳陽,作者更是手到拿來、游刃有余,八百里洞庭、荊楚大地、岳陽樓、岳陽火車站、新墻河、鐵路大橋、新墻老街、大云山、張谷英村、麻布大山等等這些帶有標志性古今建筑,一一成為小說中眾多人物活動的舞臺,有的甚至還是抗戰時敵我雙方的重要軍事據點和指揮中心。
至于雜記,作者的用意則更為深長。凡有所及史料、風俗、文物、遺址……作者都不厭其煩悉數娓娓道來,原來作者在做拍攝一部影視作品的腳本準備。此前在文學上還沒有一部關于新墻河“大捷”的長篇小說問世,而今卻還差一部影視或文旅實景大片面世。這或許就是《烽火兵王》溢出文學,而帶著雜記的初心和緣由吧。
四、以“大時代觀”匯入,活色生香鏈接“傳奇敘事”的價值與趣味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8月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要不斷推出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的精品力作,書寫中華民族新史詩。《烽火兵王》無疑是謳歌英雄、謳歌全民族軍民抗戰的宏大敘事文本,然而作品卻從人性的角度挖掘主人公曹錫“怎么由一個農家子弟、一個普通士兵,克服了對戰爭的恐懼,怎么提高射擊本領,怎么在艱苦的環境下,甚至在敵人施放毒氣的情況下,堅固掩體,保護戰友與自己的故事。”作者并沒有故意拔高、神化他們,而是貼著人性寫了他們的內心世界,寫他們的言行舉止,以細節和心理的真實,寫出了這些人物的成長經歷和偉岸精神。這樣既保持了作品激昂的旋律,又符合普通人的情感與認知;既避免了抗日神劇化,又避免了歷史虛無主義的泥沼。
特別要提及的是,這本“兵王”傳奇敘事還帶有強烈的網絡小說色彩和氣息,在結構上可能不是那么嚴絲合縫,然而整篇敘述卻讓人讀著“過癮”,比較適配年輕人的閱讀訴求。從“超文本”到“超鏈接”,《烽火兵王》的傳奇敘事具有時代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成為傳統“傳奇”創新敘事路徑的一種探索吧。
“烽火”明滅,“兵王”屹立。在“極廣大、盡精微”的歷史敘述中,在“新墻河”的歷史鏡照下,在《烽火兵王》的文本內外,一名上等兵由是完成了屬于他自己的歷史轉身,鑄就了他的不朽英雄傳奇。
真實、新穎、細膩的抗日敘事
任福階
這是一部真實、新穎、細膩的抗日敘事佳作,讓人感同身受,血脈僨張,反復回味,頗受教益。
一是堅持“真實”的記述原則。《烽火兵王》中的主要人物、重要戰事,包括時間、地名、經過都真實可信。比如小說主人公曹錫,其事跡《大公報》《中央日報》等都有報道,地方史料都有記載。曹錫是當之無愧的“兵王”。此外,如國軍第52軍2師師長趙公武,第37軍95師師長羅奇,劇(戲曲、詞)作家田漢,軍需官萬質彬與其妻子謝四六,抗戰時期岳陽縣的三大漢奸童夭生、蘇省清、費竹如,日酋第6師團11旅團今村勝次少將等,這些正面人物、反派人物及其事例,均有據可查,真實存在。書中第24章《營田營田》,描述國軍因紀律松弛麻痹大意致營田失守,日寇殘殺2000余中國軍民及其駭人聽聞的獸行,完全真實。該書還原歷史本來面目,符合長篇歷史小說的體例要求,更提升了人們的閱讀興趣,增加了作品的厚度與價值。
二是配制“新穎”的故事內容。因年代久遠等原因,曹錫的資料較少:全家務農,母親多病,共7兄弟,他是長子。1937年,27歲的曹錫結婚僅3天,就替父從軍,無后代……
歷史小說畢竟是小說,必須進行再創作。在史料基礎上,作者進行合理虛構,使小說故事更加豐富:構設了陜南特委地下黨員亢學梅,她與曹錫及其妻子韋素英是私塾同學。曹錫當兵后與亢學梅偶遇,很是親熱,被韋素英知道后誤解,韋素英就與夫弟千里迢迢來岳陽尋找曹錫。這是小說的主線,外加幾條副線,演繹出愛恨情仇、驚心動魄又合符情理的故事。窮兇極惡的日寇、苦難善良的百姓、慘烈無比的戰斗……特殊年代的人間煙火,悲歡離合,讀來張弛有度,新穎別致。《藤原日記》章節,創新性地收錄了鬼子兵藤原參加南京大屠殺的5篇日記,它點燃了抗日將士們的沖天怒火。再如,該書開篇有“人物小傳”,書中收錄了較多的、附有文字說明的珍貴歷史照片,輔助閱讀,亦顯新穎。
三是追求“細膩”的藝術風格。《烽火兵王》對主人公曹錫的家鄉陜西,對第一次長沙會戰涉及的岳陽等自然環境、景觀傳說乃至歷史文化,都花了較大篇幅,作了細致入微的描寫。作者下筆的意圖明顯:擁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好河山,豈容日寇踐踏!
該書行文細膩。在《戰王街坊》章節中,作者不惜筆墨,詳細敘述曹錫帶領謝小羊長時間拼命加修戰壕……才頂住大炮的轟擊。鬼子大量發射毒氣彈,曹錫無奈扒下犧牲戰友的衣服做成“口罩”,用小便澆濕后遮擋口鼻……毒氣使戰友們傷亡殆盡……曹錫把兩件衣服浸透水后撈出封住地堡入口,隔斷毒氣的侵襲。這些無不體現了對日作戰的異常艱險。全書多次出現戰士甘永小用軍號吹奏《義勇軍進行曲》,在曹錫犧牲和全書結尾吊唁烈士時亦如此,這非重復,而是貫穿全書的核心,昭示中國人民抵抗侵略的決心。
銘記和紀念烈士,是為了在家國危急之時涌現出更多的勇士。崇尚英雄,才會英雄輩出。當今世界并不太平,戰火紛飛,生靈涂炭,時刻聞見。倘若某天,強敵入侵,你我能否像曹錫等眾多英烈那樣臨危不懼,年輕的握槍上陣,年老的送子參戰?還是無動于衷?還會出現童夭生、蘇省清、費竹如之類的漢奸嗎?國難當頭,關鍵時刻,一念之差,天壤之別!這是《烽火兵王》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
山河為證 愛情長存
舒常敏
翻開徐載滿小說《烽火兵王》,每次讀著讀著,都會淚濕衣襟。此書最震撼我的,不僅是宏大的民族氣節,更是那植根于平民百姓中,看似渺小卻無比堅韌、專一永恒、深沉而不糾纏的愛情。作為一名女性讀者,書中那份在國仇家恨中淬煉出的、深沉而偉大的愛情,蕩氣回腸,尤其令我動容。
《烽火兵王》除了讓我對民族英雄、抗戰烈士的崇敬之外,更增添了對普通士兵的深深敬仰。它有力地證明:并非站在山頂,才能夠被看見。英雄不必立于山巔,任何地方、任何身份的凡人,都能在關鍵時刻閃耀光芒。
曹錫與韋素英的愛,超越了生離死別的痛苦,在戰火中淬煉得如山河般遼闊,如日月般永恒。他們的靈魂相契,無需言語維系,如同光譜自然交融。而亢學梅對曹錫的愛同樣可歌可泣。她知進退,在革命征途中找到了有力的支撐點。她將愛化為鼓勵和守護,在戰斗中超越自我。
尼采曾言:“人類的生命,并不能以時間長短來衡量,心中充滿愛時,剎那即為永恒。”多年追尋“愛情該是什么樣子”的答案,終于在徐載滿的《烽火兵王》中找到了——那是戰火中相互守候的忠貞,是家國大義前無私的支持,是陰陽永隔后依然不滅的思念與承諾。這份以山河為證、在血與火中長存的愛情,正是人類情感最崇高、最永恒的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