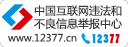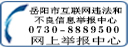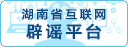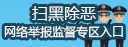□曾君華
“青山處處埋忠骨,何須馬革裹尸還。”每念及這句詩,我的心便被一種深沉的凝重與傷感包裹。那是歷史的厚重與家國的赤誠交織的情感,仿佛能穿透歲月的迷霧,望見無數英烈在民族危亡之際挺身而出的背影。而我的兩位伯父——曾惠元、曾其元,便是這千萬忠魂中,讓家族魂牽夢縈的名字。
我的父輩深植于岳陽縣新墻的土地。那片被新墻河滋養的鄉土,曾是湘北抗戰的前沿陣地。在那個烽火連天的年代,日寇鐵蹄踏碎華夏安寧,家國存亡的吶喊響徹云霄。父親是家中六兄弟里最小的一個,兒時每到中元節,他總會在裊裊青煙中鋪開黃紙,鄭重寫下亡者的姓名,包括兩位奔赴戰場后杳無音信的四哥曾惠元、五哥曾其元。父親說,抗日戰爭爆發時,四哥、五哥剛讀完私塾,兄弟倆毅然放下筆墨,穿上軍裝,加入國民革命軍第10軍,奔赴衡陽保衛戰的前線。
父親在我13歲時便離世,家族的往事隨他的離去漸漸模糊。我只記得,父親多次向我描述,在20世紀40年代初抗戰勝利前夕,家中六兄弟最終只剩父親一人孤苦伶仃。1961年,在兩個兒子離開二十多年之后,奶奶臨終前口中喃喃念著“惠元、其元該回來了”;1976年,在兩個哥哥離開近三十年之后,父親彌留之際仍記掛著他的四哥和五哥,這份跨越三代人的牽掛,早已不是簡單的親情羈絆,而是一個家族對為國獻身者的永恒惦念,是普通人對“忠魂”二字最樸素的注解。
多年來,我像追尋星辰的旅人,在歷史的塵埃中打撈伯父的痕跡。父親的老同學劉端芳老師在日記中留存的挽聯,清晰記載著奶奶葬禮上父親寫下的“二兄赴國難,千里未歸魂”;比我大30多歲的堂兄曾君錫記得6歲時在新墻河車站送別的場景:兩位叔父穿著挺括的黃軍裝,軍帽下的眼神亮得驚人,塞給他發餅時說“等打跑鬼子,叔帶你吃甜酒湯圓”。這些碎片拼湊出的,不僅是兩位年輕人的模樣,更是那個年代千萬青年“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絕——他們或許從未想過自己會成為英雄,卻在用生命踐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誓言。
我曾踏遍湘北的土地尋找答案:20世紀90年代初拜訪新墻的國民黨老兵,他們雖記不清具體姓名,卻拍著胸脯說“新墻河出來的兵,打衡陽時沒一個孬種,子彈上膛就沒想著回頭”;在南岳忠烈祠撫摸冰冷的紀念碑,指尖劃過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時,我多么希望能找到熟悉的名字;聽聞臺北忠烈祠供奉著40萬忠魂,我曾致信時任臺灣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盼著能在39萬英烈名冊中尋到一絲線索,卻終究石沉大海。可每一次失望,都讓我更加確信:伯父們或許沒有留下姓名,卻早已將“忠誠”二字刻進了民族的基因。
轉機出現在2025年6月一次偶然的聚餐中。同事的兄長閑談間偶然提起DeepSeek的數字技術可用于歷史文獻檢索的趣事,我忽然閃過一個念頭:它能否幫我找到伯父們的蹤跡?當我在抗戰歷史數據庫中輸入“尋找衡陽保衛戰陣亡的曾惠元、曾其元”時,屏幕上的文字讓我熱淚盈眶:新墻河抗戰紀念館藏有2005年村民捐贈的《陣亡士兵家書抄錄本》,其中記載“曾家兩兄弟自新墻河入伍,同赴衡陽參戰,1944年夏失聯”;《岳陽縣志》英烈表中1944年陣亡的“曾紀元”(新墻鎮人,步兵團上等兵),經當地文史專家推測為“曾其元”的同音誤記;更明確提到衡陽保衛戰中岳陽籍陣亡官兵1132人,其中7對兄弟兵里,目前僅3對留有完整姓名,曾氏兄弟的存在有高度可能性。這些文字像一束光,照亮了歷史的縫隙——原來他們的犧牲從未被遺忘,他們的名字或許模糊,卻早已融入“湘北子弟血沃衡陽”的壯闊史詩。
我立刻聯系新墻河抗戰紀念館館長,將線索截圖標記發送。館長說紀念館正在進行史料數字化整理,那本家書抄錄本或許因年代久遠暫未完成掃描,但他已將信息同步給兩岸抗戰歷史研究志愿者,并鄭重承諾將兩位伯父的姓名列入紀念館英烈紀念墻,同時向上級主管部門申報烈士名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尋找二位伯父參加衡陽保衛戰的事跡,不僅是為了家族的圓滿,更是為了讓“為國捐軀”的精神被看見、被銘記。就像岳屏山上那七千無名烈士的骸骨,他們或許沒有墓碑,卻共同鑄就了民族精神的豐碑。
如今我仍在等待消息,卻已不再焦灼。八十多年前衡陽保衛戰的硝煙早已散盡,但伯父們那代人用生命捍衛的“家國大義”,始終在歲月中熠熠生輝。他們或許只是千萬士兵中普通的一員,卻用最珍貴的生命詮釋了“忠”的含義——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危難時刻的挺身而出;不是顯赫的功名,而是“舍小家為大家”的無私。這種精神,早已融入曾家的血脈,也融入每個中國人的骨血。
我期待著伯父們的名字能被正式載入史冊的那一天,但更明白:無論是否找到確切記載,他們“寧死不當亡國奴”的骨氣,他們“甘將熱血沃中華”的赤誠,早已是家族最珍貴的遺產,是民族永不褪色的精神燈塔。歷史不能忘記!中華民族在烽火中鑄就的抗戰偉業更不能忘。那些在民族危亡之際挺身而出的英雄,那些在槍林彈雨中前赴后繼的背影,那些為守護山河而流淌的熱血與付出的犧牲,早已鐫刻進民族的精神基因。這或許就是對“青山處處埋忠骨”最好的注解:忠魂不朽,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