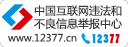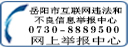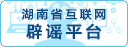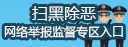(1966年9月18日,穿上軍裝的第一張照片)
□洞庭葦風
今年八一建軍節,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8周年的日子,也是我穿上軍裝、走進軍營的第59個年頭。每當這個莊重的節日來臨,心底總會翻涌著特別的情愫——那些年少時的蟬鳴、鄉路的塵土、長江的風,還有第一次穿上軍裝的滾燙記憶,總在這時格外清晰。而最讓我念起的,便是當年從華容老家出發,一步步走向軍營的那段路。
1966年立秋日,蟬兒扯著嗓子唱得正歡,天氣仍然炎熱,我和生產隊的社員們正貓著腰忙著修整渠道溝,剛插上的晚稻正盼著灌水。忽然聽見路邊老槐樹下自行車鈴聲不斷,“叮鈴鈴”穿透蟬鳴,郵遞員向大家招著手,大伙兒把手里的鋤頭和鐵鍬一扔,呼啦啦全圍了過去。隊長搶著要報紙,有人扯著嗓子問有沒有自家的信,郵遞員卻揚著手里一個牛皮紙信封,喊我父親的名字:“張大伯,恭喜恭喜喲!”
我心里“咯噔”一下——初中畢業考試剛過,家里窮得叮當響,高中想都不敢想,只填了中專。父親接過那牛皮紙信封時,邊角早被汗浸得發皺。“張勝清,被廣州軍區絕密學校錄取,請于8月20日到華容縣委招待所報到”,鉛字印得清楚,紅印章亮得晃眼。“絕密學校”四個字一出口,叔叔伯伯們立馬炸了鍋,巴掌往我肩上拍得咚咚響:“勝清要當解放軍啰!”
回家的路上,父親捏著通知書的手直抖。母親在灶臺邊忙午飯,聽見我要出遠門,鍋鏟“哐當”撞在灶上,話沒說,眼淚先滾進了鍋里。弟弟妹妹圍著我轉圈,二姐挺著大肚子從婆家趕回來,摸著我的頭說“出門要懂事”,往我手里塞了1塊錢,話沒說完就捂住嘴哽咽。臨出發前兩天,大姐帶著姐夫來了,掏給我5塊錢和一個指甲剪;表哥遞來一個天藍色塑料皮日記本,他叮囑我:“記著常寫家信。”
8月20日天剛亮,母親煮了雞蛋。15里路,父親提著我的硬塑料袋子走在前頭,大姐、二姐和母親跟在后面,我和姐夫、表哥、弟弟打打鬧鬧,一大家子熱熱鬧鬧送我出門。
到了縣委招待所,翁教員笑瞇瞇地迎出來,不光免學費,還塞給我6塊錢:“這是8月份的津貼,以后每月都有!”我哪見過這么多屬于自己的錢?手心全是汗,趕緊抽5塊塞給父親。他接過錢,眼圈一下子紅了。
天快黑時,姐姐、姐夫和表哥他們陪母親回了家,父親留下接著送我。第二天五更,教員喊集合。縣汽車站的雙節長途車像條大蜈蚣,我踩著踏板往上爬,腿肚子直打顫。父親和其他送行人站在車旁,他把斗笠壓得很低,我扒著車窗看他,他抬手抹臉的動作,隔著玻璃都看得真真的。汽車鳴笛時,他往后退了兩步。車駛過華容大橋,我再回頭,橋頭上只剩下個小小的黑點了。
太陽剛冒頭,汽車迎著東方跑,金晃晃的光灑在車頂。我們9個華容來的學生伢子湊一塊兒,你戳我一下,我推你一把,誰也沒提想家。車過三郎堰站,有人指著路邊的棉花田喊:“跟我們隊里的不一樣!”翁教員站在過道上笑:“到了地方,比這稀罕的多著呢。”
中午到洪山頭長江碼頭,風里帶著腥氣。翁教員先領我們吃過午飯,就望見輪船鳴著長笛靠岸。他認真講了乘船的規矩和安全事項,我們剛找到座位,船又鳴笛離岸,順江而下。
我們都是頭回出遠門,頭回坐汽車、輪船,頭回見長江。剛坐定就躥上頂層,江風一吹,渾身舒坦。江面上貨船多,我們瞪著水面看,總盼著能撞見江豬子(江豚)。船到岳陽碼頭時,天早已黑透了,水面上星星點點全是燈。上岸踩在石板路上,兩邊燈光昏昏的。教員領我們到岳陽縣委招待所,岳陽的幾個同學早到了。
第二天晚上,我們在岳陽火車站登上火車。火車也是頭回見,更別說坐了,新鮮得心里直跳。每站都停,上下車的人不多,車里干干凈凈。列車員提著長嘴大鐵壺,不時過來給我們倒開水,和氣得很。天亮后,車窗外的景致勾著我的眼——鐵路邊的房子、田里干活的人,都跟我們村不一樣。
8月23日下午到了地方,一輛解放牌軍車把我們送到學校營地。這兒四通八達,沒圍墻,沒哨兵,幾棟平房看著平平常常。可這是“絕密學校”啊,初來乍到,我啥也摸不著頭腦。
我們華容和岳陽的,一起分到三中隊。一個中隊十二個班,100多號人同住一間大房子,里面整整齊齊擺著雙層床。隊長、教員、區隊長,都跟我們住一塊兒。
到營房的下午,教員讓我們十幾個按高矮排好隊,區隊長和教員給大家發被服軍裝:蓋被、墊被、床單、蚊帳、背包繩、衣服包片、掛包、水壺、飯碗、兩套夏季軍裝、一個紅五星帽徽、兩副紅領章……這一下全副武裝起來,心里又高興又激動,臉上的笑都藏不住。
排隊領東西時,我排倒數第二,領到的衣服是四號,鞋子是五號。接著,區隊長和教員教我們疊被子、別帽徽、戴領章,整理內務。洗漱、洗澡、上廁所離營房有五六十米,洗漱間是敞著的棚子,一排排的水泥小池整齊劃一。洗澡間在屋里,沿墻排著水龍頭,一年四季全是冷水。
食堂在禮堂里,以中隊為單位開飯,各中隊的方桌條凳都擺在大禮堂里。幾百人吃飯,安安靜靜,連筷子碰碗的聲音都很小。
就這么著,我走出了華容。9月份發6元津貼時,我把從家里帶來的所有衣服,連短褲和那個硬塑料小提包,全寄回了家,包裹里還塞了10塊錢。學校還請來攝影師,在食堂外走廊以墻壁為背景,大家排隊照相,家里正等著看看我們穿上軍裝的樣子呢!
頭一個月,隊列訓練緊得很。訓練越累,越想家,想父母,想弟弟妹妹。有時夜里躲在被子里,眼淚悄悄往下掉,不敢出聲。
教員和區隊長好像看穿了我們的心思,每天晚飯后,總帶著我們在大操場打籃球、做游戲,嘻嘻哈哈鬧一陣,心里想家的念頭就淡了些。
我們不再是農村來的學生伢子了。穿上軍裝,戴上帽徽和領章,我們是軍校學員。被子要疊成“豆腐塊”,領章要戴得端端正正,吃飯要安安靜靜,走路要挺胸抬頭。那些第一次坐汽車、輪船、火車的新鮮,那些初到軍營的懵懂,慢慢變成了對“學員”兩個字的認識——這不僅僅是一身軍裝,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
后來我常想,1966年那個蟬鳴的秋日,攥著6元津貼走出華容的瞬間,其實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嶺。從踩著泥土的鄉路,到踏上長江的甲板、火車的鐵軌,再到軍營的訓練場,那些“第一次”的新鮮里,藏著的是少年走向成長的腳印。而那身軍裝,不僅武裝了我們的模樣,更在心里刻下了:從此,要像個軍人一樣,站直了,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