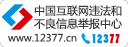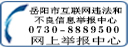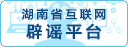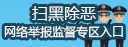□ 張長江
2005年9月初旬,平江街上出現(xiàn)過一道風景線:抗日老兵朱錫純老人,身穿志愿者送給他俏色運動服,頭戴紅色鴨舌帽,胸前戴著國家頒發(fā)給他的金光閃閃的“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六十周年紀念章”,昂首挺胸,在大街上漫步。好英俊!好瀟灑!
朱錫純1924年生。按平江的風俗,大家都喊他“錫老子”。錫老子瘦高個子,由于早年受部隊專業(yè)訓練,走路腰桿筆直,盡管滿臉滄桑,兩眼卻炯炯有神,人顯得精明、干練,年輕時肯定是個大帥哥。
記得是20世紀90年代的某一天,朱錫純來找我。我那時擔任平江縣圖書館長。他拿著一疊厚厚的、用普通橫格材料紙書寫的書稿,他說:
“這是我寫遠征軍的一本書稿,請你幫我看看,指導一下! ”
我的天!一個老兵出身的老農民,讀書不太多,竟寫出一本近三十萬字的長篇紀實文學來,令我十分驚訝。我細讀了,作者帶著深厚的感情和強烈的責任心,寫他十七歲起,參加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五軍新編第二十二師當兵,然后跟著部隊,進入中緬印三國交界處的野人山。那是一片從未開發(fā)的原始森林,瘴氣彌漫,不時滂沱大雨……在這種環(huán)境下,與日軍交戰(zhàn)。他以生動樸實的文字,細微的描寫,系統(tǒng)地講述了遠征軍在斷糧、疫情、螞蟥、毒蟲、猛獸甚至伴死尸睡覺的惡劣環(huán)境下,殺日寇、除緬奸,九死一生。末后,一個師只剩下五分之一的人走出野人山,師長戴安瀾壯烈捐軀。遠在延安的毛澤東,發(fā)表《五律·挽戴安瀾將軍》:
“外侮需人御,將軍賦采薇。師稱機械化,勇奪虎羆威。浴血冬瓜守,驅倭棠吉歸。沙場竟殞命,壯志也無違。”
作為士兵,朱錫純九死一生,雖然七處負傷,最終僥幸回到祖國。
他在作品中,熱忱歌頌了戰(zhàn)士們誓死抗日,為國捐軀的鐵血精神,詳細記述了此中的艱苦卓絕!
朱錫純曾把書稿送到岳陽,請作家張步真先生看過。1963年,張步真在平江縣安定區(qū)工作,朱錫純那時是區(qū)里的拖拉機司機,互相都熟悉。張步真先生提了許多修改意見,現(xiàn)在是修改后的稿子。
我佩服朱錫純驚人的記憶力,時隔六十多年了,他不但把遠征軍宏觀戰(zhàn)略、部隊上層人物如史迪威、戴安瀾、杜聿明等人寫得清清楚楚,還能將自己身處他鄉(xiāng)異國所經過的山谷河流、戰(zhàn)術行動,記錄得準確全面,真不簡單。
朱錫純本人的經歷,也是一部活著的歷史。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他進入汽車學校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到湘潭運輸公司開汽車。1962年“大辦農業(yè)”,他回到老家平江縣三市公社三星大隊務農。因他修車技術好,又將他調到三市公社、后來又到安定區(qū)農機廠修汽車、修拖拉機,還兼任農機站會計。工作兢兢業(yè)業(yè),多次受到上級的表彰。他多才多藝。在業(yè)余時間,他喜歡讀書,而且讀得極細。一本《紅樓夢》,讀完后他能畫出一張地圖,榮國府、寧國府、大觀園、怡紅院、瀟湘館、稻香村等等,方位座向,都清清楚楚。他會講四川話、云南話、粵語、國語,有時會甩幾句簡單的英語。他還會唱京戲,一曲《空城計》,字正腔圓,京味十足……
對于他的書稿,我也提過一些不成熟的建議。他不斷地加工修改,反復打磨,從未放棄。2010年9月,抗日戰(zhàn)爭勝利65周年的時候,《野人山轉戰(zhàn)記》終于由北京新世紀出版社出版發(fā)行。出版后反響強烈,作品是二戰(zhàn)史的一個實例,被認為填補了二戰(zhàn)史的部分空白。
北京電視臺青年女記者李紅慕名來到平江,采訪《野人山轉戰(zhàn)記》的作者朱錫純。這給朱錫純極大的鼓舞,當記者了解到安徽省某地還有一位名叫劉桂英抗日女兵仍然健在,與朱錫純是同一個部隊,當年兩人曾同過野人山,李記者便想促成他們二人見面。這時朱錫純已經76歲,李記者帶著老人去縣人民醫(yī)院做了體檢,確認身體可以外出,便同朱錫純一起乘火車來到安徽,兩位抗日老兵55年后重逢,那激動是不言而喻的。他們又一同前往安徽省蕪湖市鏡湖區(qū)公園,拜奠了抗日烈士、他們的老長官戴安瀾將軍墓。共同回憶過野人山往事,感慨萬千。北京電視臺播放了這部紀錄片,許多省電視臺也予以轉播,影響很大。
《野人山轉戰(zhàn)記》出版后,朱錫純自己留的存書很少。一些老兵之家、抗日人員家屬,以及一些社會人士,紛紛聯(lián)系朱錫純索購此書。朱錫純原先工作過的湘潭運輸公司的領導來平江慰問他時,就要去了幾十本。他便給新世紀出版社打電話。出版社免費又寄了一些書給他,才緩解了燃眉之急。
這時,他高興得像個孩子。
2021年3月,朱錫純老人在平江與世長辭,享年97歲。各方人士前來悼念,靈堂一副挽聯(lián)概括了老人的一生:
高風仁者壽,著書言志,春來芳草連天碧;
浩氣野人山,衛(wèi)國抗倭,君去長歌動地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