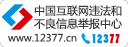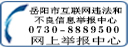□萬 明
夕照里,風柔柔地吹著,送來陣陣菊香。外甥女胡六一把一堆臟衣服塞進“小神童”牌洗衣機塑料缸,放入洗衣粉和清水,蓋上缸蓋,把開關調到“快速”的位置,立時機聲隱隱作響,哼著歡快的歌。這個時候,她往往會站在洗衣機旁怔怔出神,因為,她仿佛聽到了另一種變奏曲——遠去的棒槌聲。
外甥女的家趴在山旮旯里,一個山多水少、人多地少、麻雀子飛過不落腳的窮地方。六十年前,還在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她,母親撒手而去,體弱多病的父親既當爹又當媽,獨自承載著沉重的枷鎖。白天荷鋤下地干活,傍晚料理瑣碎的家務之后,干起女人的活來。右手挽著裝滿臟衣服的竹籃,左手提著極原始的洗衣工具——一根尺多長、茶盅口般粗、一頭大一頭小的結木棒,去池塘邊浣衣。那時鄉下普遍用不起肥皂之類的奢侈品,只好用“麻枯 ”(一種榨過茶油的圓餅去污)把一件件用水浸泡過,擦過“茶枯”的衣服,攤在塘邊的條石上,一邊翻動衣服,一邊高高揚起棒槌反反復復地捶打,發出沉悶的“咚、咚、咚”聲,震得山響。然后,把捶過的衣服在水中抖凈,再撈上來擰干水漬。洗完衣服,汗水在他臉上和手臂上流淌,洗衣的辛苦和沉重的夢全鐫刻在池塘透明的水波上。
花開花落,花落花開。外甥女出落成一個大姑娘,與上門女婿結婚了。家里的公牛不生崽,她接連生了四胎。俗話說,居家怕五口,七口之家壓力大不說,光是每天七號人的漿衣洗衫就夠吃力的了。她從父親手中接過棒槌,繼續扮演著浣衣的角色。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她樂此不疲。棒槌聲聲,哼唱著一支古老而又難以知曉的歌謠。她俯下身子,揉碎了池水中的倒影,手在池水中起起落落,水花濺去老遠。夏日,正逢雙搶時節,為多掙幾個工分,披著霞光出,踏著月色歸,一身汗水一身泥,沖個涼后,匆匆提盞小煤油燈去浣衣。冬天,大地冰封,她用棒槌敲開池塘里厚厚的冰,凍僵了的手握不了棒槌,哈哈熱氣,還是無濟于事,只能將手塞進棉襖里暖一暖。雙腳蹲在硚石上,時間久了,又僵又麻又痛,于是站起來,使勁跳一跳,舒展舒展筋骨。
一次發大水,塘堤被沖垮了,塘里的水全部溢出,她只好去對面的小河浣衣。小河離家一里之遙,河水泛黃、混濁,她雙腳泡在齊膝蓋深的水中,在裸露的石塊上捶呀捶,冷不防,棒槌從手里滑落,被浪沖走,卷入漩渦。情急之下,她奮力去追,一頭栽入下游的深潭中,要不是丈夫及時趕到,差點丟了小命。她心里涌動著一種說不出的苦衷:棒槌呀,在即將與你分別的時分,你給我留下的只是苦澀的回憶。
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春風吹來,改變了外甥女一家的命運。大女兒中專畢業后,吃上了“皇糧”,跳出農門,進了城。二女兒招工成了“公家人”。三女兒在長沙開美容店,當老板。最小的兒子自辦網站“淘金”,收入不菲。生活雖有大改觀,但漿衣洗衫的事卻成了難題,因新居附近既無池塘又無小河,棒槌已派不上用場了,自家也掘了一口井,她便買了塊木質擦衣板,勾腰弓背伏在木盆旁,繼續著她的營生。然而這玩意使用起來并不輕松,手掌磨起了老繭,且速度比棒槌慢了半拍。
日子就這樣又過去了好些年。
2019年春暖花開的時節,村子里通了自來水。外甥女喜上眉梢,點點的笑靨上都像綻開鮮艷的桃花,她便拼命打扮起自己的“羽毛”來,建起了二層樓房,添置了整套家具,購買了三星牌大彩電、海爾冰箱、格力空調,全是國內外名牌,實實在在“奢侈”了一把。最引人注目的是,利用“家電下鄉”“以舊換新”的契機,把使用不久的單桶洗衣機換成名牌全自動洗衣機。有人不解,她神采飛揚,說,如今吃講營養、住講寬敞、用講高檔,有了鈔票,就該好好享受一番。這全自動洗衣機不僅速度快,洗得干凈,而且甩后有八成干,只需稍微晾一晾,省時又輕松。
從棒槌到擦衣板再到洗衣機,這質的飛躍,只是農村日新月異變化中的一個縮影。
“啪啪啪”,悲戚單調的棒槌聲遠去了,已被歲月的河流慢慢沖淡。“咚咚咚”,耳畔傳來十四億人奔向新時代的強大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