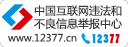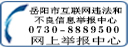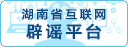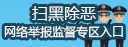□陳有紅
“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每到丹桂飄香的中秋佳節,我便會想起這首古詩,小時候邊吃月餅邊聽故事的場景也隨之浮現在腦海。
正值“七歲八歲狗都嫌”的年紀,我剛聽父親講牛郎織女的故事沒幾天,又催著問母親,還要多久才有“嫦娥奔月”的故事聽。前幾年雖然聽不懂,但對故事的印象有點深。母親撫著我的頭用滿口的南邊話說:“紅伢兒呀,那要到農歷八月十五,中秋節賞月的時候才有聽的。”
其實,母親心知肚明。兒子要聽故事是假,想吃月餅是真。
七夕后一月有余,我望得流涎的節日快到了,父母親早早地把菜園里種的苧麻扯了,刮凈曬干。農歷八月十五那天,天剛麻麻亮,父親就去商店把苧麻賣了,換回了半斤肉和兩個月餅。
那時的月餅像發餅一樣大小,四周是一圈整齊的齒輪,包裝特別簡單,都是用不黃不白的厚紙包著,油光發亮。我趁父母親不注意,忍不住偷偷地摸了一下,舔了一口,還叮囑妹妹不要跟父母親說。
晚飯過后,皓月當空。我和妹妹依偎在母親身邊,母親不停地為我倆搖扇驅蚊。父親將月餅一分為二給了我和妹妹,然后帶著幾分神秘,又講起了嫦娥奔月的故事。故事還沒講完,我和妹妹的月餅就吃沒了,父母親把另外一個月餅又分給了我倆。
月餅吃完,我和妹妹還在津津有味地舔著粘在手上的殘渣。父親知道他講的故事我們肯定沒太聽,又不厭其煩地重復著關于月亮的故事:嫦娥、玉兔、吳剛,還有桂花樹……
我身為人父時已是20世紀80年代,物資開始豐富了,中秋節吃月餅成了理所當然的事。
月餅年年翻新,從外到內也出現了質的飛躍。富含文化元素的包裝美觀精致,其內容更是豐富多彩,有豆沙餡的、草莓味的,還有蛋黃、五仁、哈密瓜餡等等。
每到中秋節那天,只要天氣晴朗,我和老伴就會學著父母親,盡可能把兒媳和孫伢們邀在一起賞月。在陽臺上放一張桌子,擺上水果和各式各樣的月餅,但從不用刀切。因為月餅多的是,有自己買的,也有朋友送的,且規格各異。然而,不知怎的,不僅我沒有了小時候的那種貪婪,孫伢們也一點都不饞,打量了一下月餅后,就都仰望著如玉如盤的月亮,豎起耳朵要聽故事。
平心而論,父母親極少讀書,給我講的故事都只講了個大概,我也只聽了個大概,若不是長大后從一些書籍資料中補充完善,我真的要卡殼了。我從八月十五吃月餅的故事,講到嫦娥奔月的傳說,孫伢們個個聽得津津有味。兒媳們也情不自禁地吟起詩來:“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調皮的孫兒也學著爸爸媽媽搖頭晃腦地吟誦著,把兩個孫女逗樂了。
賞過了月光,月餅卻紋絲未動。想想過去,是先吃月餅后賞月光,賞了月光還想吃月餅。而現在是先賞月光再吃月餅,都像不想吃月餅了似的。
“好吃,好吃,來,大家都開始吃吧!”老伴見月餅未動,帶頭拿了一個嘗了一口,還順手遞了一個給我。兒媳、孫伢們見狀,才慢慢品嘗起來。我接過老伴手中的月餅,心情久久難以平靜。暗想:“要是父母親都在該多好啊!屬于父母親的那份月餅我怎么也不會占為己有了。”此時,如晝的天空似乎如我心思般出現了愁云,月亮也躲進了云里。